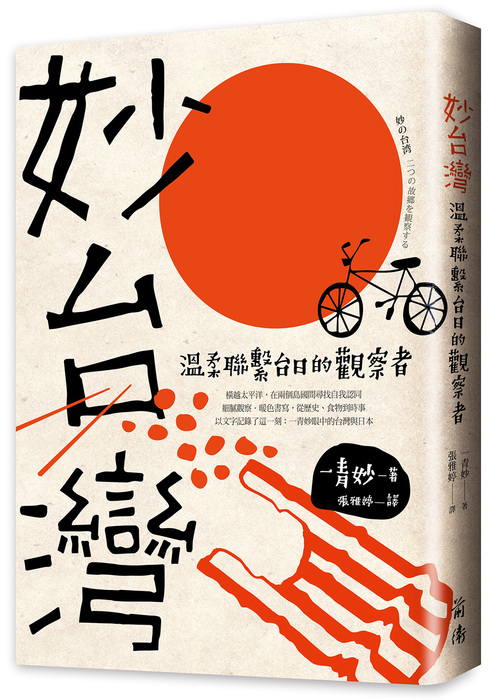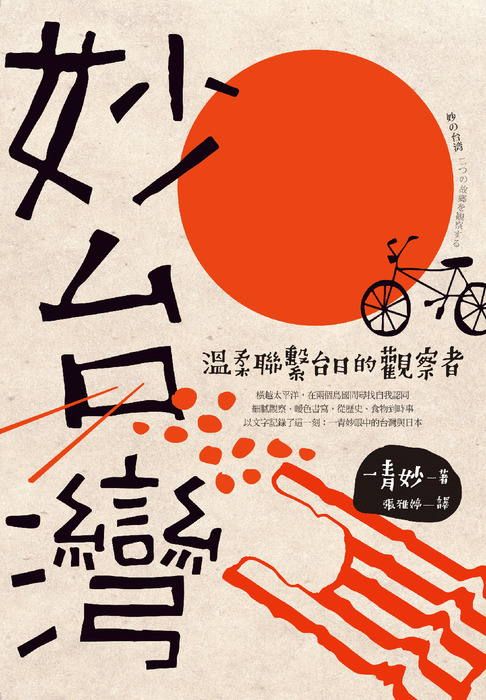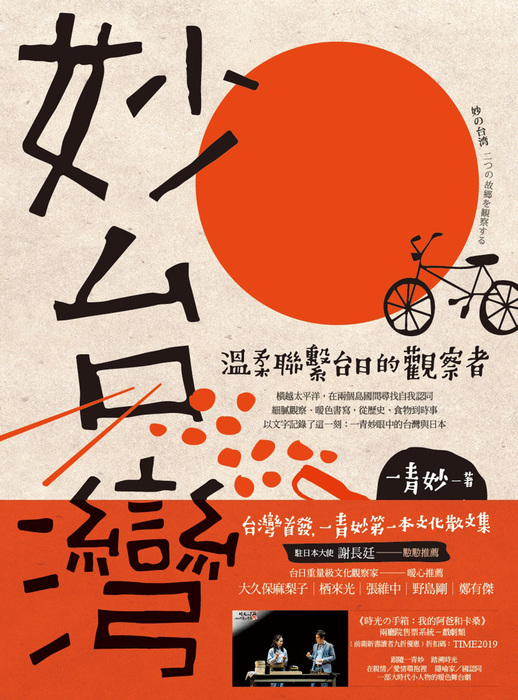〈我寫,我演-一青妙作品終於搬到台灣舞台劇〉
我的工作是寫作和演戲。我把家族的故事寫成書,之後原作被改拍成電影。在那部電影裡,自己也稍微露臉,演了個小角色。這次則是搬上舞台劇,在舞台上我將擔綱主角之一的「自己」,也就是一青妙。
想來,自己真的很幸運。
他人看來,也許會覺得自己演自己很蠢。但希望大家能見諒,老實說,有這個可以詮釋自己的演出機會,我感到非常幸福。現在,我人在冬季的台北,每天都在排練舞台劇中度過。
這幾年,因為工作或私人因素頻繁往返台日;兩地都是我的故鄉,這種感覺逐年越來越強烈。但是,唯獨這一趟來到台灣繃緊神經,戰戰兢兢。因為二〇一九年三月要在台北上演舞台劇《時光の手箱:我的阿爸和卡桑》,這是我在台灣第一次參與的舞台劇,為了排練,預計會在台停留大約三個月之久。
當我在台灣開始排練時,首先驚訝的是對待劇本的態度不同。劇本是舞台劇的基礎,到目前為止,我在日本參與演出的舞台劇,大多是重視劇作家描寫的世界,包括劇本裡的每句台詞,甚至連標點符號都得忠實呈現。可是,這次的舞台劇,演員遇到難以表達的台詞,可以轉換為自己覺得通順的說法。
「咦,有這一句台詞嗎?」「奇怪,怎麼和上次不太一樣……」
起初我感到困惑,但現在已完全適應。每次輪到自己講台詞,多少也會出現微妙差異,但排練確實比較容易進行。可是,這樣真的沒關係嗎?大家好像都覺得沒差,劇作家似乎也不以為意。彼此溝通意見,彈性應對,真像台灣作風。以成果來看,有時反而能雕琢出更好的作品。當然,像日本那樣,依照一開始就決定好的劇本,按部就班地排練,讓人安心。不管是那種,都各有優缺點。果然還是和國民性格和民族性有關。
這部舞台劇的原著是拙作《我的箱子》和《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這兩本書以我已逝的雙親為主角,以散文描寫家族記憶。二〇一七年拍攝完成的日台合作電影《媽媽,晚餐吃什麼?》也由此改編。這部電影不只在台日,也在香港、泰國等地上映,並獲邀參加各國電影節的展映。我想一切都要歸功於提議拍成電影的白羽彌仁導演、演員和觀眾的支持。
接著,這一次作品將以舞台劇的形式呈現。
當朋友聽到要搬上舞台劇時,驚訝地問道:「怎麼決定要改編成舞台劇的?」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清楚。
距今約三年前,我與台灣的電影導演李崗見了面。當時,我以《我的箱子》中文版代替名片遞給了他。二〇一五年,李崗完成了電影《阿罩霧風雲》的拍攝,題材是描寫戰前活躍於台灣的五大家族之一「霧峰林家」。我們見面時,是他正在考慮將其他家族的故事搬上大螢幕的時期。我的父親出生於五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我的作品剛好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起初計畫要拍紀錄片電影,可是在考究細節的過程中,有不少知道顏家歷史的耆老已經過世,苦惱於如何選定核心人物,有段時間失去聯絡。就在連我自己也完全忘了紀錄片這回事時,再度接到聯絡。
「打算用舞台劇的方式呈現。」雖然改用舞台劇演出是我沒料想到的形式,接下來的進展卻很快上了軌道。
負責編劇的詹傑是出生於基隆的三十多歲青年,他形容自己會寫這部舞台劇的劇本是「很有緣分的事」。他透過顏家歷史,開始瞭解自己生長居住地的過去,發現故鄉新的一面。他分享了這番感受,讓我聽了深感欣慰。
他涉獵了大量資料,在劇本裡充分反映連結台灣和日本的歷史,並把在日台間動搖的我的家族真實面貌,處理得十分細膩。
對於活躍於在電影領域的李崗而言,這也是他首次擔任舞台劇監製。他懷抱著滿腔熱情,提出作品的方向性或演出等的意見,也經常出現在排練現場。
在開始排練的前一天,所有相關人員齊聚,彼此認識。大家先輪流自我介紹,輪到我時,腦筋卻一片空白,至於那時說了什麼,其實不太記得。我身兼原著作者和演員兩種身分出席聚會,平常我不太會緊張,可是這次的心情卻多了幾分戒慎恐懼。
時代背景的設定從二戰結束前後的一九四〇年代到現代。因為時代橫跨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戰後的日本和台灣,還有現代,為了更加忠實呈現時代演變,台詞主要使用日文,加上台語和中文。
我的角色是扮演現代的「一青妙」。來到台灣的一青妙為紀錄片導演說明活在日本和台灣之間的雙親回憶。飾演導演的是資深舞台演員朱宏章,他也是台北藝術大學的教授,大家稱他為「老師」。其他還有飾演母親親友的資深演員謝瓊煖。我希望藉此機會從他們身上學習演技,並活用到日台演技工作。自己演自己,加上台詞幾乎都是中文,對於以日文為母語的我來說,真是一大挑戰。心情是一半期待一半不安。
實際排練後,令人驚訝的事也越來越多。原來台日可以如此不同,覺得很新奇。比方說,排練場地。我在東京多次參加的排練場地,因為擔心隔音問題或是周邊住宅區的條件,通常在地下室,即使是地面上的空間,也幾乎沒什麼窗戶。一天可能有大半時間都待在排練現場,但是空氣不流通,揮之不去的霉味,環境絕對說不上舒適。
相較之下,台北的排練場地位在被樹木環繞的建築物二樓,有開放的落地窗。光是來到排練現場,心情也跟著明亮起來。不只是排練場地,台灣的寬廣道路以及寬敞的建築物,都讓人瞠目結舌。希望日本也能仿效這樣的都市設計。
我的不安是來自於如何演自己。我的舞台演出經驗超過二十年,但這是頭一遭自己演自己,而且從未想過。每當在採訪中被問到:「作為演員,最有趣的地方是?」我都是回答「能成為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可是這次是自己演自己。
「那不就更容易了?」希望各位不要這麼想。因為要客觀看待自己很困難,如法國詩人阿蒂爾.蘭波(Arthur Rimbaud,1854~91年)說的「我是別人」(Je est un autre)。所謂的當局者迷,看不清自己的往往其實就是自己。因此,每天的排練都在和自己對抗。
舞台劇集結充滿魅力的人,每個人都很有個性。飾演父親・顏惠民一角是鄭有傑。鄭有傑的父親原本在日本生活,直到三十五歲才回台,包含台灣人母親,家裡以日文對話。鄭有傑的父親一直到過世為止,習慣講日文,看日本電視和報紙。雖然年代不同,其實和我的父親十分相似。聽說當他收到演出舞台劇邀約時,認為是「命運的安排」,當下就答應了。順帶一提,鄭有傑的哥哥現在仍來往日本和台灣,兄弟間講電話也是用日文。
受到父親的影響,鄭有傑講了一口非常流暢的日文。但是,這是他第一次接到台詞幾乎都是日文的工作,因此和我一樣緊張。
母親.一青和枝的角色是由日籍演員大久保麻梨子演出,她和母親一樣,都嫁給台灣人,現在以台灣為據點,活躍於演藝圈。
即使時代改變,決定與不同國籍的人攜手共度一輩子,遠嫁國外的心情,個中滋味只有親身經歷才能體會吧。而且,大久保學會中文,台語也很流暢,由她擔綱這個角色,再適合不過了。
飾演其他角色的演員,例如和日本女性結婚的資深演員楊烈、和台灣女性結婚的米七偶、取得日本舞踊修業證書的王楡丹等人,他們在現實生活都和日本有很深的淵源。
排練通常從下午一點過後開始,中間晚餐休息一小時,之後再持續到晚上十點左右。
根據分配到的角色,有時不必排練,或只需要參與下午或晚上的某個時段,有彈性調整的空間。其中,最辛苦的莫過於要一直待在排練場地的「演出家」。
日文的「演出家」,在中文稱為「導演」。在日本,執導電影的人是導演,而執導電視劇或舞台劇的人則是演出家,在台灣則統一稱為「導演」。
導演是掌握舞台命運的關鍵人物,由現年約三十五歲的廖若涵負責執導,我聽說她是位年輕新銳的實力導演,相當活躍。我想像著日本的演劇界以嚴格指導出了名的導演蜷川幸雄,已有了不時被劈頭大罵的覺悟。但完全不是那回事。她是靠稱讚讓演員成長的導演,也因為如此,所以有時聽到她較為嚴厲的指教時,就像是吃了辛辣的花椒,全身發燙。
而我最開心的莫過於排練一結束,大家就各自鳥獸散,有些人回家,或趕赴另一個工作。在日本,比起「個人」,更加重視「群體」。即使是排練,也經常遇到必須要等誰結束了才能回家,或有人提議要聚餐卻很難拒絕之類的情形,隨時要在意別人的眼光,這種情形很常見。對於崇尚個人主義的我來講,形成了莫大的心理壓力。
在台灣,排練結束後,東西收好的人就先走了。比起「群體」,由此可窺見台灣社會是以「個人」優先的吧。這一點正合我意,能實際感受到我也流著台灣人的血,難怪如此契合。觀察越多,越覺得台日有很多地方不一樣,真是有趣。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首場將在台北市松山區的城市舞台演出。舞台上會出現原作裡沒有的登場人物,也包括我在書裡無法描寫的內容。透過舞台劇,觀眾有機會重溫日台歷史,注意到每個家庭裡家人存在的理所當然,體會到家人的重要性,哪怕只是一丁點的契機,對我而言是何其榮幸。
排練還要持續到三月上旬的公演。接下來,我一邊期待著日台演劇文化差異的新發現,一邊享受在台灣首次登台演出的過程。並且希望這齣大量使用日文的舞台劇,有天也能在日本上演。我懷抱著這個願望,在二〇一九年的新年,雙手合掌向神祈禱。
〈台灣人父親與日本人母親留下的禮物―—電影《媽媽,晚餐吃什麼?》上映〉
「妙ちゃん、ごはんできたわよ。」(小妙,可以吃飯了喔。)
大螢幕裡,自己的小名不斷地被呼喚著。女演員飾演「我」的角色,還有母親一青和枝、父親顏惠民、妹妹窈……,我的家人陸續登場。
在參加完台日合作電影《媽媽,晚餐吃什麼?》的試映會後,我的心情不是有趣或感動,而是充滿著難以言喻的不可思議感。「是這樣子的嗎?」我問我自己。
這部電影改編自約莫五、六年前寫的作品《我的箱子》和《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中文版皆由聯經出版)。台灣人父親和日本人母親結婚、我在東京出生後不久,就舉家搬到台灣,在當地學校就讀。十一歲的時候,全家的生活重心移到日本,在日本就讀國高中,從齒科大學畢業,直到現在。
我之所以會寫書,和家人有很大關係。父親在我十四歲那年過世,母親在那七年後也撒手人寰。家中和台灣有關的父親不在,與父親那邊親戚有聯繫的母親也不在了,之後我與台灣的關係頓時變得疏遠。
我再度開始意識到台灣的存在,其實是這七、八年的事情。起因是位於東京都內的舊居──過去和父母親、妹妹四人一起居住過的地方,要先拆解後原地重建。我在整理衣服、書籍和鍋碗瓢盆等食器……各式各樣的東西時,發現一個不曾見過的箱子。深紅色的木箱,約A4紙張大小,我搖晃了一下,裡面發出聲音。戰戰兢兢地打開箱子,看到大量家人在台日之間的書信往來、家人照片,還有母親一面照料罹癌父親,一面持續寫下鬪病過程的日記。甚至還有母親在台學習台灣料理的食譜。
深紅色的箱子就像時光膠囊,我的腦海裡一一浮現家人間的記憶,不斷地滿溢出來。
一九二八(昭和三)年出生的父親,當時台灣還在日本統治下,生於屈指可數望族的長男,是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日本人」。父親寫的信裡,最後一定是用舊假名的「さよふなら」(再會了)作為結尾,交友圈也幾乎都是日本人。
然而,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戰勝國的父親與戰敗國的友人一夕之間被區分開來。父親變成了「中國人」,但是不會說中文,因而迷失人生的方向,一直到死之前似乎都還在為身分認同而苦惱,經常把自己關在房間。如果是以現在來看,應該是憂鬱症吧;當時還是孩子的我,縱然感到奇怪,卻無從得知理由為何。
然而,在細讀箱裡一封封的信件後,我才知道父親背負著繼承家族事業的壓力,還有無法符合周圍對他的期待等的苦惱,他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在母親遺留的鬪病日記裡鮮明記載著,當父親被診斷出末期肺癌時,母親顧慮到父親的精神脆弱而不告知病情,所以父親直到過世之前都故意忽視母親,完全不開口跟她講話的模樣,以及母親的苦惱。
雙親留下的遺物,我一個個拿在手上,驚訝於自己的一無所知,於是動了想要再度認識台灣的念頭。
睽違已久的台灣,街頭的模樣已經改變許多,但是舌尖依然牢記食物的美味,身體也很快就適應空氣的味道,台灣曾經是我的一部分,那種感覺立刻甦醒。我試著追尋父親的腳步,把再訪台灣的體驗寫成散文,集結成《我的箱子》一書。
另一本書《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是以母親為主角。對日本而言,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是陌生而疏遠的土地。家人們擔心母親遠嫁他鄉而不會再回日本,可是她不顧反對,決定與台灣人的父親共結連理,隻身來到沒有任何親友的台灣,作為大家族的長媳,母親一面努力獲得認同,拚命學習如何烹飪台灣料理。
放在廚房櫃中箱子裡的食譜,裡面記載著三杯雞、涼拌黃瓜、滷豬腳、蘿蔔糕……等,台灣傳統家常菜的作法。不管哪一道,都是從我小時候開始就經常出現在餐桌上的母親味道。打開食譜,有一種像是和母親重逢的感覺。
父親喜歡喝酒,豐富多樣的下酒菜是必備的,嚴格說起來是大男人主義的類型。母親是家庭主婦,每餐幾乎都為父親煮了六道以上的料理。即便到現在,我吃飯時還是習慣配上很多道菜,全然是根生於小時的飲食生活。
電影《媽媽,晚餐吃什麼?》是描寫透過母親的台灣料理連結起一家子的日常生活。即使雙親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但是對兩位女兒的關愛從來就不曾少過。雖然是極為平凡的家庭故事,但也是一部有助於理解台日之間複雜關係的作品。
二○一一年發生的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台灣的賑災捐款高居世界第一,在眾人記憶裡留下深刻印象。之後台灣和日本的民間交流也越來越興盛,年假的海外旅遊目的地票選活動,台灣入選為最受歡迎的地方。女性雜誌或電視節目也經常介紹台灣的美食和觀光景點。
在台灣,還保存著許多日治時代的建築和文化。為了讓更多日本人認識濃厚的人情味,充滿懷舊風情的台灣魅力,我肩負著位於台灣南部的都市.台南親善大使的使命,在日本各地進行演講活動。
在醫療方面,台灣和日本也有很深的關係。台灣自一九九五年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是以日本的「國民皆保險制度」為範本,二○○四年起推行IC卡化等,甚至超越了日本。台灣也面臨了少子化、高齡化問題,嚴重程度更甚日本,但是從很早以前就引入外籍移工,作為看護、幫傭,在銀髮族照護現場相當活躍。今後,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或許有不少的台灣經驗可以作為日本的借鏡。
我擔任牙醫師,平常往返樂齡設施進行看診服務為主。在二戰結束後不久出生的母親,生活在物資缺乏的環境,有過因為營養失調而瀕死的經驗。或許也是這個原因,從小牙齒不好,在我上大學時,前排牙齒就已幾乎都是假牙。
「這樣子,媽媽就不用擔心牙齒了。」
當我考上齒科大學時,媽媽如此說道。這句話我到現在還忘不了,可是母親在我畢業前夕即過世,沒辦法親自幫媽媽看診,是我最大的遺憾。
在設施裡,可以一面幫老人調整活動假牙,一面慢慢傾聽他們說的話,我自己也很享受那些和爺爺奶奶閒話家常的時間,或許是我把他們和我無法再見面的雙親重疊了吧。
因為雙親留下的「箱子」,我對過去的回憶得以一一拼湊起來。還有,埋藏在箱裡有關雙親的故事也搬上大螢幕。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箱子」,只是形式不同。希望這部電影可以作為契機,喚醒觀眾隱藏在箱裡的重要記憶。